公司从设立到注销的整个周期是持续性的,也是静态与动态相互穿插、相辅相成的。就公司之设立事项,设立发起者或各股东之间就待设或已设公司的出资方式、出资期限、增减资、分红方式、退出条件等重要事项和各方之间权责权益必将有一系列约定和安排,并最终会形成众多对应类别的协议或文件材料(就前述提及协议或文件材料,以下统称“股东间协议”)。
按一般商业逻辑,在公司设立后,各股东共同签订生效的股东间协议中的各项条款都会尽可能地吸收转化为公司章程中的条款,公司章程作为相关约定的载体,是股东间就投票表决权、分红权、设置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有关公司治理的“特别协议”,亦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所约束的“股东间”的协议。
实务中,股东们为了某些特别的需求,往往会先仔细、认真地起草、修订股东间协议并签署,但在随后的公司设立登记过程中,简单对市场监督管理/工商部门提供的章程模板进行略微调整后就提交,以期更快的通过审核并成立公司,从而导致股东间协议中很多意思自治的条款无法真正被公司章程吸收,也导致了公司章程内容与前述提及的一系列相关协议约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矛盾。
鉴于企业形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笔者在本文仅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设立的企业作为分析对象,对股东就股东间协议约定的出资形式与公司章程约定不一致的情形所引起的纠纷,进而衍生至对股东间协议和公司章程效力优先顺序的争议核心点进行剖析和建议。我们先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4日做出的一起二审判决作为参考案例:
案号: (2020)京03民终119号
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股东A)
被告:股东B
案由:股东出资纠纷
股东A与股东B于2016年2月18日签订一份《公司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约定A以货币方式出资1000万元,占公司50%的股份,B以“相关市场、人脉资源和项目平台产品技术”等技术方式出资,占公司40%的股份,并约定“本项目的其他规定,由公司章程规定,如公司章程没有本合同约定内容,或与本合同约定内容相冲突,以本合同约定为准。”双方于2016年3月15日完成公司工商登记,《公司章程》约定,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A认缴出资额600万元,B认缴出资额400万元,出资期限均为2016年12月1日。A完成了出资义务,B未完成出资义务。虽然《公司章程》与《合作协议》约定不一致,但了解到B所谓的技术方式出资实际上仅是一种管理方式和技术支持,不是合法出资方式,为保证双方能得到互惠互利的合作,双方确定仍然保持各自持股比例,但调整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
依据《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按期足额缴纳出资,是股东的一项重要法定义务,必须严格履行。本案中,A和B作为公司的股东,在成立公司前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公司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金额,并且约定公司章程的内容与协议内容不一致的,以该协议为准。虽然该协议的签订时间早于公司章程的形成时间,但因A和B在签订《合作协议》时并未有公司章程,而且公司自始仅有一份工商登记机关备案的公司章程,故《合作协议》中记载的公司章程,显然是指公司在成立时向工商登记机关备案的公司章程。
此外,尽管公司主张《公司章程》是对《合作协议》出资的调整,但综合本案来看,欠缺调整的合意,如按公司的主张,其无法解决《合作协议》与《公司章程》约定冲突的问题,而该冲突背后,实质上是股东之间内部纠纷。
判决: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公司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股东B向公司缴纳出资40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股东B负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从上述案例中可见,在公司设立过程中,部分股东会以其所具备、具有的“社会资源”“独特的技术”等非实物、非标准化的方式出资,该类出资方式也常见于中小企业,但却与《公司法》第二十七条[1]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2]的规定相悖。此类出资形式由于未满足公司法、公司登记条例对实物出资“可评估性、可转让性”的规定,往往无法在工商部门处满足其章程备案的要求,故仅能通过股东间协议对此类出资形式和对应股权进行详细约定。
此种情形下,股东出资虽然违反章程约定,但未违反股东间协议约定的情况下。对此,我们归纳、整合法院在本次裁判的思路如下:
(1)“根据公司法‘双重标准、内外有别’的原则,……司法实践中,处理公司纠纷,应当区分公司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分别适用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当公司内部之间发生争议的,以实质要件为主进行认定;当公司外部之间产生争议的,则以形式要件为主进行认定。”[3]本次的股东间协议为股东真实意思表示,故本案中,应当以股东间协议约定为准进行裁判。
(2)“股东间协议约定一方股东以技术出资,该技术出资股东所持股份对应的注册资本金由控股股东以货币方式替代缴纳,以符合公司法中对于出资形式的规定和设立登记的要求,系股东内部对于实际出资金额与占股比例作出的约定。该约定并不因为违反公司法中关于出资形式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4]
纵观2019至2021年三年期间的股东出资相关司法判例,法院裁判思路在此类案由纠纷中,从“对章程的约定优先”逐步转换为“基本支持股东间协议的约定内容”。从法院的认定来看,在股东出资纠纷的案件中,股东的权利义务一般在股东间协议中有较为具体的约定,且股东间协议一般规则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条款管辖;而公司章程的效力则多由《公司法》体现。两部平行的部门法,是相辅相成而非对立的,股东间协议或公司章程应视不同案由而解读不同的解释优先顺序位阶。在股东出资纠纷的案由中,当股东间协议与公司章程出现矛盾时,一般优先以股东间协议约定内容来调整当事人间的矛盾;而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对外公示的文件,在于登记机关登记备案后即对股东、公司以外的第三人产生效力,在公司与第三方产生争议时,一般以公司章程的约定作为首要解释顺序。
由此,笔者认为,有限责任公司更加强调人合性,因此股东间的协议约定对于公司的正常运行起到了更大的作用,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和关注,故股东间协议与公司章程约定矛盾时,不宜单方面强调公司章程的效力,我们建议可以按如下顺序对相关解释顺序的约定进行审核:
1. 股东间内部产生的纠纷:
(1)当股东间协议与公司章程列明了一致的优先解释顺序,则按相关顺序解读;
(2)当股东间协议与公司章程列明的解释顺序不一致,或均未约定解释顺序时,则以后签署生效时间者为准。
2. 对外(第三方)产生纠纷时:
(1)不论股东间协议是否披露给第三方,原则上,以章程约定为准;
(2)若章程列明股东间协议优先的,则以股东间协议的约定为准。
同时,为避免因股东间协议与公司章程约定内容相矛盾而给股东、公司带来不必要的隐患,甚至产生纠纷对各自和第三方的经济、信誉等产生损失和损害,笔者建议如下:
1. 重视并确保起草章程时候的专业性和完整性,尽量使股东间协议的约定被公司章程吸收转化;
2. 如出于公司实际经营考虑,股东间协议的部分条款之约定可能违反《公司法》中强制性条款的,则建议在公司章程中列明“如本章程与股东间协议不一致或未列明之处,以股东间协议的约定为准”;
3. 如股东间协议的补充协议涉及对公司章程的实际修改,应在签署生效后尽快制作相关决定文件和章程修正案,并于工商部门进行章程变更登记。
最后,考虑到各公司均有各自商务上的特殊安排,且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较高的“人合性”,笔者在此提醒各股东可在股东间协议或章程上明确优先解释的位阶,并着重对出资相关义务、投票表决权、分红权等重大事项进行合理的转化和明确的约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修正) 第二十七条: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16修订)第十四条:股东的出资方式应当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但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
[3] 摘自【(2019)川民终953号】法院判决书“法院认为”段落。
[4] 《人民司法·案例》2021年第5期第72-7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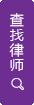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4998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4998号